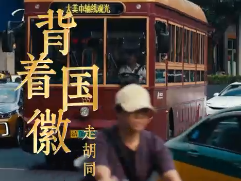“在案子沒有處理完時,心里像是有一塊石頭壓著。(調解)當天,也沒覺得這條路怎么樣。在看了現場基本情況后,給雙方做思想工作,差不多調了一個早上。也是像今天這樣的大雨,坐在田棚里面調解。”7月22日下午,法官前往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陽梯田深處,就一起涉梯田相鄰用水糾紛調解案件進行回訪,記者隨行采訪。


對法官來說“沒啥”的一條路,卻讓記者一行汗如雨注。踩著碎石泥巴路,一腳深一腳淺的,管得住腿管不住腳底,稍不注意就會踩到熱乎新鮮的原生態糞肥。
“這也算是(路況)好的了,之前還有個梯田糾紛案,像這樣的小路都沒有,法院去的每一個人都摔到田里了……”聽完法官一席話,一行人繼續埋頭“行路難”。
穿過叢林已耗費大半體力,入眼一大片翡翠綠,刺眼的陽光來不及躲避,還帶來紫外線灼燒的微痛感。
“現在的背對背,是為了將來還能面對面”
這一類涉梯田糾紛很是常見,“敢破壞我的田,就不讓你家牛通行”。原、被告兩家承包的梯田相鄰,被告在上方,原告在下方。此前,被告家的牲口經過原告家水田,時常會踐踏農作物,為此,原告架起圍欄不準牲口通行。而后,被告將自家水田出水口改道,使得原告家水田無法正常灌溉,改種玉米地。雙方爭執時有發生。

圖為案件回訪現場
抵達糾紛現場后,原本晴朗柔和的天空,風云變幻間,凝聚起厚厚的積雨云,大雨侵襲從不提前打報告。法官微微一笑道,這在雨季的云南是家常便飯。
吳仙,云南省元陽縣人民法院法官,土生土長的哈尼人,擅長用哈尼語跟涉梯田糾紛的雙方當事人作溝通。即使辦案多年,她面對當事人也依舊帶著大姑娘般的靦腆微笑,有一回甚至連當事人都沒有認出她就是辦案法官。
同樣的大雨,同一片梯田,將吳仙的思緒拉回調解當天。“我記得調解當天,有一方本來是要走了,說要回去干農活了,不想再調解了。我就跟他說,下這么大的雨,哪里也去不了,不如就在田棚里面聊聊天噶……”

法官對案件進行現場調解的田棚
一場調解,在瓢潑大雨的梯田田棚里進行著,驟雨時下時停,仿佛也帶著情緒在叫囂著要發泄。一調就是三四個小時,在家長里短和釋法說理中,大雨澆滅了當事人的對立情緒。
吳仙說:“其實涉梯田糾紛處理的都是鄰里關系,年輕一輩子女都不在場,守田老一輩鬧矛盾的居多。有時候因為你罵一句我懟一句,往往就是嘴邊多說了那么一句話,情緒上頭了,互不退步沒法調解。”
記者:那當時您說了什么,最終觸動了他們呢?
吳仙:“鄰里之間沒必要鬧這么大的矛盾……兩家的梯田世世代代都在這里,你自己也背不走,你的后代也背不走。后人在地里干活,還不是要面對面,有時候還需要對方幫忙。”
哈尼人自古就是勤勞的農耕民族,他家谷子需要收了你家去幫忙,你家玉米亟待撇了他家來幫忙,團結互助是梯田農耕千年歷史鑄就的村規民約。
借用一句話:“現在的背對背,是為了將來還能臉對臉。”
對哈尼人來說,梯田就是命根子。為了梯田和后代考慮,雙方最終各退一步,達成調解。原告當場就把自己架在雙方梯田之間的圍欄拆除了,被告也同意日后不牽大牛以免踩踏原告玉米地。
“事情處理完回去的時候,我才感覺到腳下的路原來這么難走……”來時心壓大石塊,不覺腳下行路難,吳仙笑著回憶道,那天糾紛調解結束時,也剛好雨過天晴。法官的情緒也隨之再次燦爛。

“一輩子伺候這個水田,干得動就一直干”
“從近幾年昆明環資法庭的受案情況來看,主要還是取水權糾紛占比較多,大約占60%,其次是排除妨害糾紛,比如雙方當事人在田埂中修建擋墻引發的糾紛,此類案由大約占20%,其他比如相鄰糾紛、財產損害賠償糾紛等占20%。”昆明環境資源法庭法官助理曾佳提供了一組涉梯田糾紛案整體數據。
背依梯田這座“幸福靠山”,靠天吃飯的農耕民族,講究一個天時地利人和。每年3、4月枯水期,正逢梯田大量用水的插秧時節,也是涉梯田用水矛盾最多的時候。
“‘合’字下面有個‘口’,人與人之間鬧了矛盾要用嘴來講和,‘拉’字有個提手旁,握手言和的意思。”元陽縣新街鎮全福莊村委會黨總支書記盧衛明,也是“合拉調解室”主理人介紹道,合拉調解室日常主要調解山林水土類糾紛,每年大概有2、3件涉梯田糾紛需要調解。“合拉”兩個字在哈尼語中意味“好呢、滿意”。
據盧衛明回憶,2024年發生一起比較典型的涉梯田取水權糾紛,兩家梯田之間有一汪“龍潭水”(即山泉水,當地說法),一方想遷引龍潭水到自家梯田里,但泉水出在自家梯田里的村民卻不同意,雙方起了爭執鬧到合拉調解室。

拍攝于元陽梯田某處山泉水
“我們在現場勘察完后,就請他們到合拉調解室坐坐,講明水資源都是國家的,不是個人的,(龍潭水)大家可以共用。先滿足出泉水一方的三畝梯田用水后,再滿足另一戶需要用水的村民。”雙方接受了調解,也都表達了滿意。
梯田是命根子,水是命脈。“一輩子伺候這個水田,干得動就一直干”,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就算一年下來掙得不多,梯田也是割舍不下的根,尤其老一輩哈尼人對梯田的感情更深。

村民正在清理梯田雜草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是因為天氣不好,街上看不到村民。而是哈尼人還在你睡覺的時候,就一大早把地里農活干完了。”
涉梯田事宜不論大小,分毫必爭。據了解,村村寨寨每戶人家大概能分得3、4畝梯田,“一畝田雖掙不了多少錢,但卻是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也要完完整整傳承給下一代。”這是哈尼人一輩子的執著。
既然哈尼人有共同的追求和目標,那當矛盾發生時,自古習得的村規民約就成為了解紛的切入口。在法院引導下,村委會整合多方資源,內部直接將矛盾消融,大事小事不出村寨。

村民正在巡視梯田狀況
當問及全福莊村成為“無訟村”后有何深刻改變時,盧衛明表示,自從在合拉調解室搭建了共享法庭,附近村寨也能共享司法資源,惠及一方百姓。法院會引導合法合規地進行調解,兼顧情理法,應重要農事節點入戶宣講普法,答疑一方村民。對鄉親們來說,“不再是‘看得見的摸得著的才是真實的’,村寨鄉親們整體法律覺悟也有所提升。”
“哈尼人家的梯田會呼吸,是活著的,生長的”
“倆家族都有來,當時雙方講話都沖,為爭一口氣,情緒一時激憤,調解有難度……怕矛盾再次激化,也一直沒敢用‘侵占水田’這個詞,而是用‘妨害’水田管理和應用一詞代替。”法官理錦回憶起今年一起典型的涉梯田排除妨害類糾紛案時,眉頭微蹙,眼底情緒有些復雜。
原、被告水田上下相連,被告家水田在上方,原告家水田在下方,中間以田埂為界,被告家認為原告在梯田清理雜草過程中,向田埂內里挖深,以此來擴充水田面積,故此被告在原告家水田里修建田埂擋墻,雙方引發矛盾。

案件現場勘察田埂擋墻圖
理錦,云南省元陽縣人民法院新街中心人民法庭庭長。據她講述,該案共進行了4次現場勘驗。第一次,現場測量擋墻長寬高;第二次,現場還原前因后果,但雙方不接受調解;第三次,開庭前和執行部門碰頭,現場勘驗后評估執行難度,看如何有效解紛;第四次,開庭后又勘測現場,根據擋墻具體方位、數據等,還原整個客觀事實輔助最終判決。
“首要保證雙方利益無較大損失。被告私建擋墻,雖侵占到了原告水田,但實際有加固作用,惠及雙方田埂。既然已投入價值,已修建部分就保持原狀。最終判決,拆除尾部殘余圍墻,保留已建成的保護性圍墻。”理錦表示。
法官坦言,調解得多了不難琢磨出一點:矛盾,往往是一個時間段的情緒疊加至爆發。過了那個階段情緒便緩些,更易解紛。來法庭的村民心里多少會有拘束感,尤其是頭一回接觸訴訟的,更需要心理適應過程。

上下水田緊密相連,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鄰里關系,就算有一時矛盾也會被無限綿延的農耕文明抹平。
“法”字有水,才具柔性,如同這里的梯田。正如一位陪同采訪的法院資深干警所說:“被萬千溝渠水纏繞供養的梯田是活著的、會呼吸的,也是會生長的。”
仔細研究哈尼梯田千年農耕文明,不難發現刻入農耕民族骨子里的追求公平正義的樸素價值觀——木刻分水法、溝長制,這也為司法守護梯田遺產奠定了精神基礎。
哈尼人自古有一套水資源分配法:刻木分水。由村寨德高望重者牽頭,根據各村寨、各條溝渠所需灌溉梯田面積,約定每條溝渠應分用水量。刻木分水可保梯田不論位置高低、面積大小、豐欠水年都能得到有效灌溉。彰顯了哈尼人追求公平正義的樸素價值觀。

圖為梯田木刻分水器及溝渠
木刻分水,代表的是一種集體秩序,現已發展成完備的制度,在紅河縣人民法院“木刻分水調解室”里掛著梯田調解法,絲絲潤人心:
道法自然定分,遵循客觀規律查明案件事實
村規民約指引,利用當地公序良俗思想啟發
鄉賢智者規勸,邀請德高望重人士教育感化
多元組織聯調,借力各類調解組織合力調解
謙讓共贏止爭,互諒互讓和諧共贏解決爭議
回訪觀護事了,調后回訪鞏固徹底案結事了
千年梯田農耕生產生活中形成了一套集體無意識的村規民約“趕溝”,并世代沿習。村寨選出有聲望、勤勞務實、責任心強的人作為“趕溝人”,負責疏通梯田溝渠、分配水量、修繕溝渠、維護木刻分水器、調解梯田用水糾紛等,以保證溝渠水能流進各家梯田。現如今已進化為成熟的“溝長制”。

圖為巡視梯田溝渠狀況的當地溝長
李文才,元陽縣新街鎮土鍋寨村溝長,60歲,一人負責的水溝有三公里多。“清早5點多起,每天巡視溝渠狀況,一走就是7、8公里。”像他這樣的溝長,僅在土鍋寨全村就有11名。
哈尼人有句話:“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水資源在森林、村寨、梯田、水系中循環往復,即“四素同構”生態系統,這也是為什么梯田被稱為“會呼吸的灌溉系統”。曾佳解釋道,水是哈尼梯田的“命脈”,哈尼人將溝水分渠引入田中進行灌溉,因山水四季長流,梯田中可常年飽水,保證了稻谷的發育生長和豐收。守護好水系,就是守住了梯田的命脈,守住了哈尼人的“根”與“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