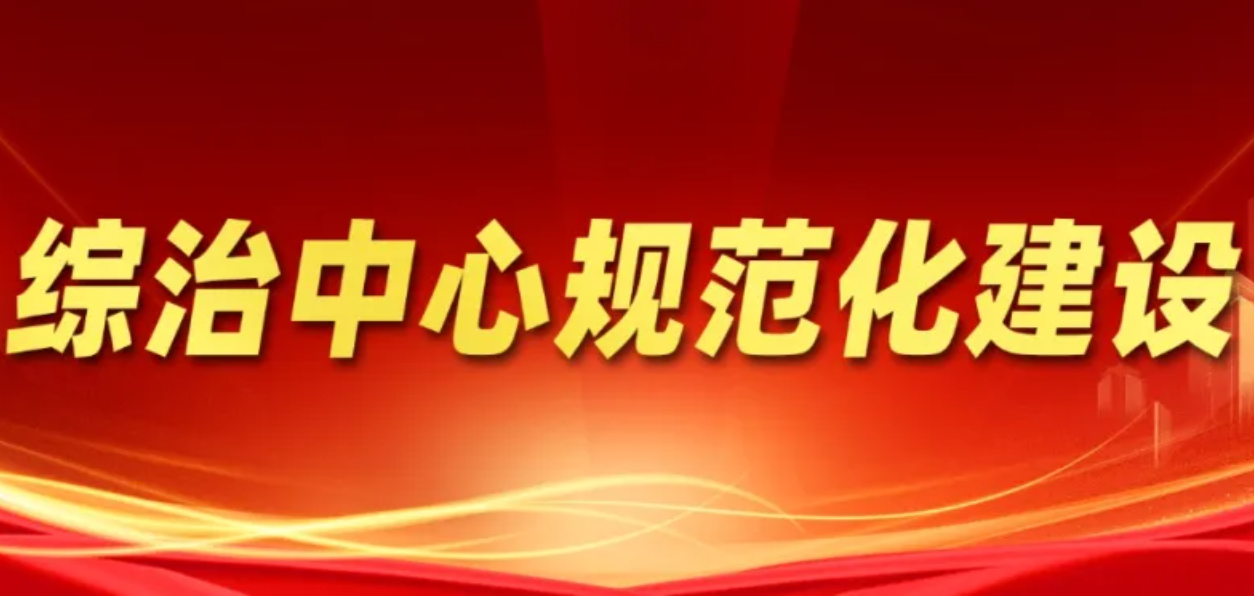京郊發生了一起造成三人死亡的交通事故,現場有一輛電動三輪車、一輛摩托車、一輛自行車,三名死者沒有任何交集,且沒有第四個參與人。難道是三輛車相撞導致三人死亡?三名死者又該分別對應哪輛車?自行車到底是推行還是騎行?事故到底是誰的責任?案件遇到瓶頸。
“清華大學博士后交警”張雷來到現場直接找到疑點“自行車的位置距離中心現場太近了”,他對三輛交通工具和三名死者又進行了復勘,通過組織開展多輪的檢驗、分析和模擬試驗,推斷出最終結論:這實際上是一起雙方事故,自行車是搭放在三輪車上的,并沒有參與到道路行駛過程中。

根據這一判斷,屬地交通支隊沿著張雷給出的方向,開展擴線調查,為明確事故責任方奠定了基礎。
現任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事故處理支隊交通事故鑒定中隊警務技術三級主任的張雷,日常工作就是根據現場遺留的蛛絲馬跡剝繭抽絲,來確定事故的發生過程,進而查明事故原因,還原案件真相,為后期的責任認定和經濟賠償提供依據,是交警中的“刑警”。
拒絕“誘惑”克服“阻力”清華大學博士后當交警
2008年,北京迎來了舉世矚目的第29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北京市公安局也乘勢而為,面向社會全面引進高學歷人才,而張雷就是這批人才中的一員。
那時,作為清華大學汽車工程系博士后,張雷曾經與北京市公安局交管部門有過多次事故鑒定和科研方面的合作,他發現,一線的鮮活案例、豐富數據是院校和書本上所沒有的。出站前,張雷就下定決心,“到基層去,在實踐中形成經驗、發現問題、總結規律、研發技術,從而反哺給社會,減少事故的發生。”
回憶起出站時的那段日子,張雷面對各種“誘惑”和“阻力”,有高校邀請他當導師、建實驗室,有汽車企業聘請他做高管、拿高薪,他都一一婉拒。

“當時我始終關注北京市公安局在交通管理工作方面的發展,了解到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成立了當時全國唯一一家省級公安交通中心,我想去那里。”張雷說,當北京市公安局負責人才引進的工作人員找到他時,自己毫不猶豫就答應了。
張雷說,對于自己這一選擇,包括妻子在內很多人并不理解,覺得搞交通事故鑒定“廟小”。不僅夫妻二人激烈討論過好幾次,張雷的導師也覺得他是做科研的好苗子,應該去國家重點實驗室搞研究,才算得上是“人盡其才”。面對各種質疑,張雷還是覺得“這個領域大有可為”。
當得知張雷這個清華博士后選擇成為交警之后,曾有人為他惋惜,而張雷卻說:“我自信滿滿而去,才發現自己所學的知識,根本不夠用,還要學。”
交通事故現場情況復雜,事故鑒定涉及的知識領域非常寬泛,包括法律、醫學、理化、刑事技術等。同時,由于交通事故產生的機理與運動相關,還需要掌握力學、圖像學、統計學,甚至還包括計算機技術和電子數據分析等方面的知識和技能。為盡快適應崗位,張雷利用一切業余時間學習新知識,甚至冒出過重回學校攻讀相關專業的念頭,奈何時間不允許,“只能在實踐中通過搞案子惡補,哪不行,就抓緊學。”
張雷在不斷實踐和學習的過程中,養成了用哲學思維去全局性、系統性、動態性地看待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習慣,創新形成了多學科、多領域交叉融合的綜合調查取證模式,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17年里 出具3萬余份各類鑒定文書無一錯漏
2009年,京郊發生了一起造成人員死傷的交通事故。前期,屬地交通大隊在發生事故的電動車駕駛座上,提取到了一處血痕,經鑒定屬于死者,據此推測事故發生時,駕駛人可能就是這位死者,但又無法排除昏迷傷者駕駛的可能。工作推進不下去,屬地交通大隊報請事故處理支隊介入,張雷被指派前去開展復勘工作。
那時的張雷加入交管隊伍不足一年,主辦民警對他的能力有所懷疑。張雷經過細致的分析,判定駕駛人是那位正處于昏迷狀態的傷者。面對主辦民警各種疑問,這位“初來乍到”的新警從容地解釋道:“交通事故現場是運動的,血痕的形態也要充分考慮運動過程中血液和車輛的相對速度、運動方式。”張雷用現場重現和模擬實驗兩種方法進行驗證,科學地解答了那處血痕的成因,又根據死者的落地位置、人體損傷特征、地面痕跡、車體痕跡、微量物證以及人與車輛的相對運動,反推死者生前并不在駕駛位。那一天,張雷的解釋和推理通俗有力,列舉的證據和鑒定結果客觀確鑿。隨著傷者從昏迷中蘇醒,其敘述也印證了張雷的判斷。
此后,張雷的名氣在北京公安交管部門甚至全國公安交管系統迅速傳開,他憑借自己廣博的知識儲備、系統的思維能力和科學的分析方法,讓一起起原本撲朔迷離的事故最終清晰明了。
17年里,他承擔過30余例全國重特大交通事故的調查和認定工作,參與調查3000余起全市各類交通事故,參與1800余起全國重大疑難交通事故鑒定,出具3萬余份各類鑒定文書更是無一錯漏。
而除了交警職業身份之外,張雷還擔任中國合格評定認可委員會技術專家,科技部和公安部科技興警智庫專家,公安部部級專家人才庫首批入選專家,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研究院能力驗證技術專家。
“知識和技術只掌握在自己手里怎么能行,要將它們轉化成為實實在在的科技裝備,才能解決問題、提升效能,從而惠及更多方面、更多人。”這是張雷始終堅持的觀點,更是他開展創新研發的動力所在。

拆掉技術操作“門檻”現場拍照后系統可自動生成所需的勘驗要素
在一起發生在外省市的特大交通事故中,張雷作為國務院特大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組專家,承擔了該起事故復勘的主要工作。面對大面積、不規則、相互疊加作用、無法有效剝離的痕跡,有什么方式可以將這些痕跡分離出來?曾經在國外學術期刊上了解過三維掃描技術的張雷,一下子就想到可以把三維掃描技術應用于交通事故現場勘查,他將三維掃描工具、拍攝設備進行了實戰優化,將現有的勘查鑒定系統進行了適用性升級,創新構建了能應用于交通事故痕跡鑒定的系統。
由于采取整體、密集的方式收集勘驗對象的特征點,檢驗的準確性大大提高,加上使用的是激光技術,保持了所有痕跡的完整性,實現了交通事故痕跡物證信息采集、比對和判定的全程無接觸、無破壞和數字化,有效解決了傳統檢驗方法難以實現的復雜痕跡的分析和場景復現等問題。這一創新技術在該起事故調查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為查清事實、確定原因、認定責任提供了核心證據。
“但考慮到系統操作門檻高、配套系統數據存儲要求高,對于大部分交通事故和基層單位來說并不適合,這項技術后來只在重特大交通事故現場勘查工作中得以應用。”他說,“好的裝備,要能解決普遍性問題,得讓基層民警上手就能用,而且實踐效果得好、應用范圍得廣。”循著這樣的思路,張雷很快尋找到了新的研發方向。
經過大量實踐和深入思考,張雷認為現場勘查最為耗時的地方,在于使用傳統工具對痕跡的大小、位置進行記錄,繪制現場圖這些環節上。
張雷從這一點入手,借鑒測繪攝影技術,將傳統直線型標尺改良為平行四邊形的標尺,在現場勘查過程中,只需把標尺擺在痕跡附近,用相機進行拍攝,將照片上傳到其研發的“道路交通事故快速處置系統”內,系統可自動生成所需的勘驗要素,從而有效縮減現場勘查的時間。
一次,北京環路上發生了一起情況復雜的交通事故,當時正值晚高峰,交通壓力不言而喻。張雷帶隊運用這項發明,將現場勘查時間壓縮到12分鐘即全部、高效完成。他說,“在以前,這樣的交通事故現場勘查最快也得用時1個小時,很容易造成大范圍擁堵,間接造成數以百萬計的經濟損失。”
這項發明后來在交通事故現場勘查工作中被廣泛應用,并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
創新裝備一個接著一個,張雷始終不滿足。在他看來,新裝備要跟得上時代的發展,滿足新形勢、新要求。

參與完成15項科研項目 有效解決我國交通事故處理重大關鍵性技術難題
在一起危險駕駛案中,現場公共圖像顯示,撞車瞬間的車速很快,可它究竟有多快,成為了司法審理過程中的一項需要著重考量的因素。但由于事故現場痕跡過于復雜凌亂,使用傳統的痕跡計算方式無法對車速進行測算,張雷決定利用視頻圖像對車速進行鑒定。綜合視頻顯示時間、畫面參照物、幀數、運動軌跡等一系列因素,他算出車輛肇事時的車速在110.6至121.7公里/小時之間,遠超70公里的限速,為案件定罪量刑提供了重要依據。
在此案的基礎上,為了適應道路公共圖像設備和車載錄像設備廣泛應用的新形勢,張雷及時將上述鑒定方法進行固化,主持制定了公共安全行業標準《基于視頻圖像的車輛行駛速度技術鑒定》并于2014年正式頒布實施,成為全國交通事故車速鑒定的主要手段。

從警17年,張雷準確把握道路交通安全事故處理國際前沿發展趨勢和我國實際需求,開展系統性的警務裝備、警務技術創新,不僅先后主持和參與制定了包括《道路交通擁堵經濟損失評估指南》《道路交通事故痕跡鑒定》《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勘查箱通用配置要求》《公安機關道路交通事故鑒定機構建設規范》《道路交通事故涉案者交通行為方式鑒定規范》在內的涵蓋公共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駕駛、事故鑒定領域的18項行業標準,讓通過這些鑒定方法形成的結論成為司法過程中的有效依據,讓相關領域企業更加注重產品安全性能的提升,從而保障道路交通參與者的安全。
特別是,作為科技部和公安部科技興警智庫專家,他率先在新能源汽車和智能網聯汽車行業生產規范和準入制度等領域開展系統性研究,承擔并完成了多項公安部相關科研課題,參與了公安部《智能網聯汽車準入和上路通行試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實施細則(試行)》的研究制定工作,推動新能源汽車和智能網聯汽車交通事故鑒定效能提升和行業規范化發展。
參加工作以來,張雷累計參與完成國家級和省部級科研項目15項,有效解決了我國交通事故處理的一些重大關鍵性技術難題,為規范我國道路交通事故辦案和司法鑒定工作做出了突出貢獻。
張雷,男,1974年9月出生,中共黨員,工學博士后,2008年參加公安工作,曾榮立個人二等功1次、個人三等功1次,獲評“北京市有突出貢獻人才”,當選2023“最美警察”,入圍2025“最美基層民警”候選人。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王浩雄